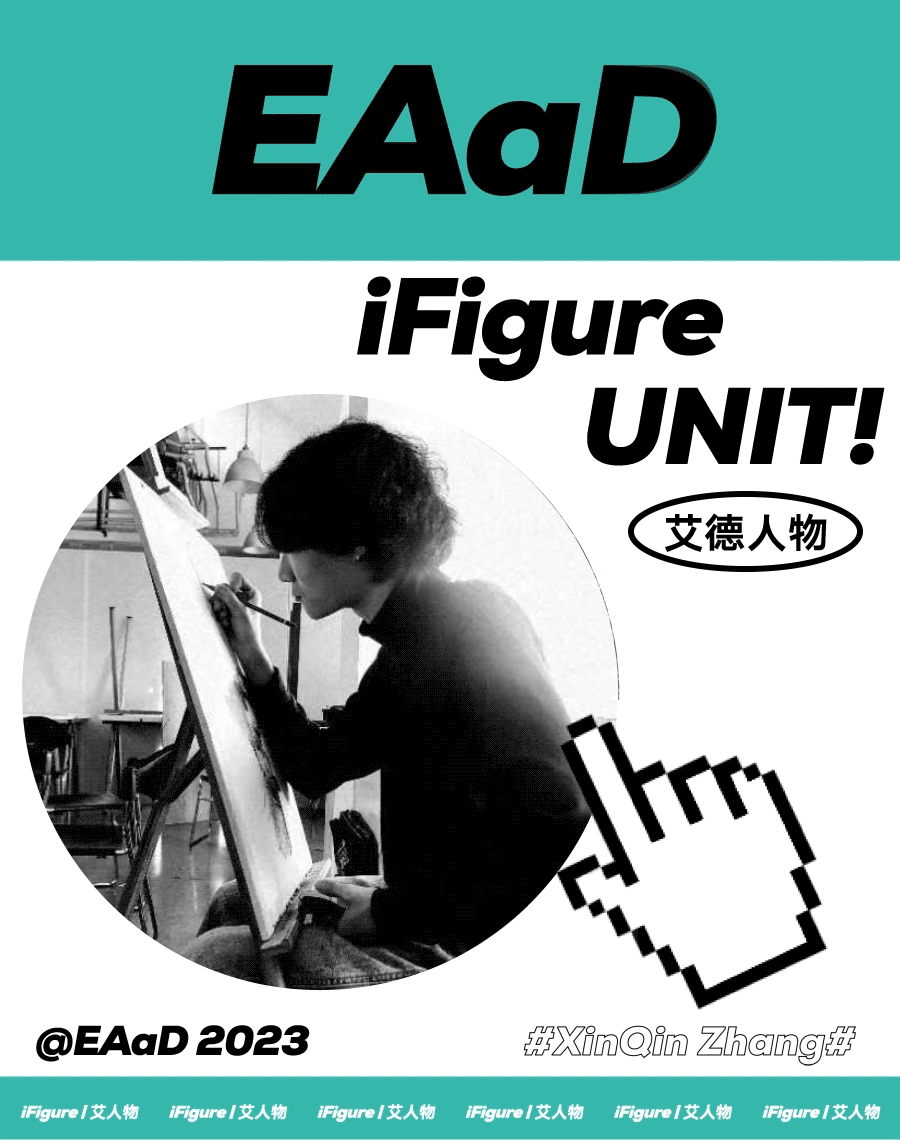
在艺术课堂逐渐被边缘化、社会追逐效能的时期,在影像逐渐平庸化的时代,在技术不断革新、影像概念逐渐被晃动的时代,我常常在想影像课堂应当何去何从。如果以技术作为落点,那么图像的生产者分分钟被科技取代;如果以观念为主体,影像又容易滑入一种当代艺术教条的语言体系,难以为设计学院的学生打开一种开放应用的可能。影像作为设计学院的基础学科,在这个具体的语境中需要被探索与赋予新的价值:镜头,作为连接“我”与“世界”的另一个窗口,成为一种主体性的观察方式——它投射出“我”是如何切入环境并生成自身的图像思维体系,它可以是感性的、艺术化的表达,也可以是科学性的、类型化的归档,它不再止步于一种结果的呈现而是回到影像生成的过程,回到“我”使用镜头进入环境的一种体验,以图像来整理思维的聚焦与持续性的发展。影像,在这里成为了一种方法为设计的感性表达与理性认知提供了一种艺术性的、跨学科的路径。

张梓钦,作为环境设计2104班的学生,是大一数字影像课里第一个用胶片拍照的人,第一个主动要求去山里采风的人,也是第一个意外将影像从课堂延伸到个人表达并获奖的人,这次也是第一次完整的展示了自己的作品并讲述自己与影像创作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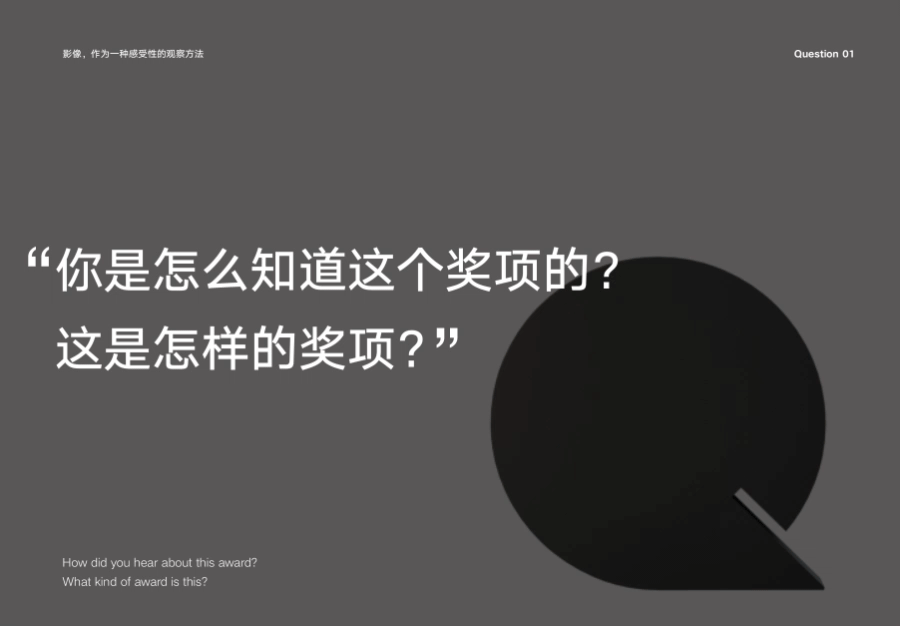
我在这个奖项中一共投了两组我的影像作品,分别是《心...》系列与《如果天空是画布,那么大地就是画笔》系列。前者为黑白胶片影像作品,具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情绪的作品。后者为彩色胶片影像作品,内容风格相对于前者而言更为理性化。
对于选择的标准,最重要的便是必须是要表达出最真实的内心情感,换句话说是可以与我的个人情感所和解的作品。对于内容与风格而言其实并没有很明确的方向,反而这次的两组获奖作品想要表达的情感,内容,风格都相比较而言很极端,这次的两个获奖作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容风格。《心...》是去年的六月份在秦岭脚下一处村庄内拍摄的。当时也是我刚接触用胶片去创作影像不久。这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不确定因素与我强烈的个人主观情感。使用了黑白的表达手法,混乱的构图,慢速快门所带来的模糊,无层次的黑与无层次的白占据了此系列中大部分内容。在当时拍摄时并没有固定的目标与头绪,只有在那个一半破败,一半繁荣的村庄中感受到的戏谑与非理性的感受。自然与破败的房屋像是在争夺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在去这村庄之前,我的内心充满了各种混乱的,负面与正面交织的情感,妄图去这个村庄去表达,释放自己。到达之后我发现这个村庄整体的非理性的氛围与我的当时的内心极其相似。于是我便抛弃了各种按下快门前需要考虑的因素,只用“心”去捕捉当时的光与影。用这像是“废片”的影像去表达我的心,去寻找混乱心境中的出路。《如果天空是画布,那么大地就是画笔》是与前者截然相反的一组作品。如果说前者是情绪丰富的,混乱的,甚至可怕的,那么这组作品便是情绪单一的,平静的,美好清新的。当我走在这个钢筋与水泥占据主体的世界时,归属感这个词在我们的世界就像是不存在的。没有所谓的自然。我们能看到的世界的造物只剩大地生长之物与天空。每当我抬头望向天空时,人工种植的花与树便与天空结合成了一组完美的画作。天空变成了画布,大地变成了画笔,大地上的生长之物变成了画中的内容。没有人的痕迹,只剩我们可以看到的自然。我便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些完美的画作。不存在构图,不存在主次,不存在技术含量。只有这些自然的画。很简单,很唯美,也很无聊。好像只是平常的花卉自然影像,但在我的眼中是自然在人占据主导的世界下做出的完美的画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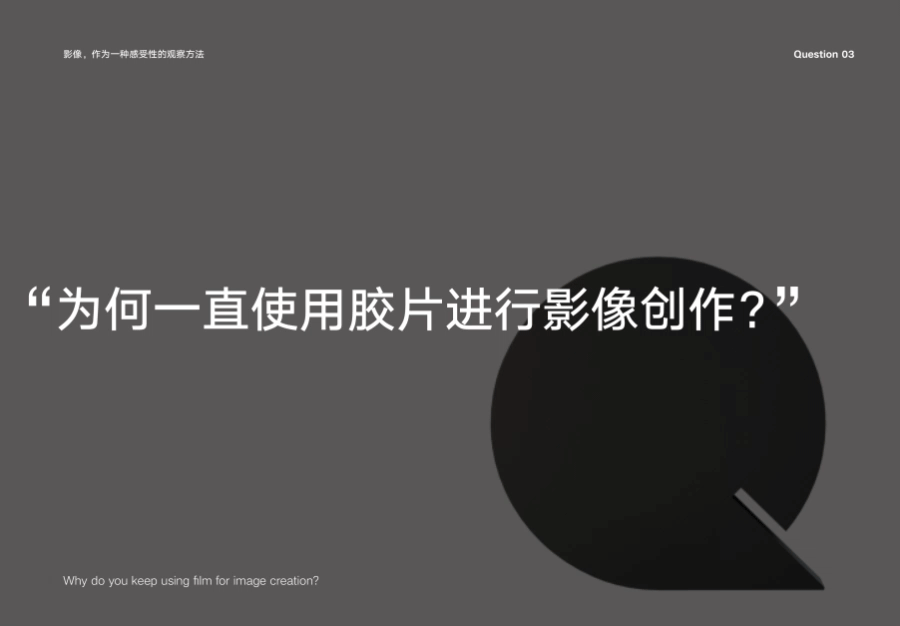
我使用胶片有多个原因,简单来讲是不确定性,多样性,永恒性与我的经历。首先,不确定性。当我们在使用数码设备进行创作时,每按下一次快门,你的作品便会完整清晰的呈现在你的眼前。我们知道自己拍了什么,自己拍的满不满意。但胶片不是这样的。拍完之后,曝光正常吗?有没有偏色?有没有拍歪?对焦有没有对好?等等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只有当胶片冲洗出来之后我们才会知道自己拍了些什么。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对我而言却是胶片的最大的魅力之一。用数码设备拍完一组作品,可能每一张都拍的非常好,但是内心的感觉却非常平淡。少了一些对我内心的刺激。但是胶片的不确定性却一直刺激着我,每拍完一卷,在冲洗完成前内心都会无比的期待。当终于看到自己的成果时,即使一卷36张有35张自己都不满意,那剩下的自己满意的一张形成的刺激是比用数码拍的全是满意的作品的刺激性更高。有时候可能拍摄失误,冲洗出来发现眼前的画面并不是按下快门那一瞬间想要的效果。但是就是这个失误反而可能会形成比我想象的更满意的影像。这,也是不确定性的魅力。再来说多样性。胶片摄影具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不同品牌的胶片,同一品牌不同系列,同一系列不同感光度.....都会形成不一样的效果,当然这是显而易见的。当一卷胶卷拍摄完,不同的冲洗方式也会造成不同效果的影像。更深入来说,拿柯达5219电影卷来讲,它是一款用来拍摄电影的灯光专用胶卷。当我把这个灯光卷拿到日光下去拍摄时,它形成的效果便非常耐人寻味,即使是温暖的日光也可以变得冷峻。当故意欠曝时,它便会偏色发蓝,形成更加特殊的效果。当一个胶卷过期时,它本身的效果又会发生变化。如我之前拍摄的柯达5248电影卷,它已经不知过期了多久,时间赋予了它独特的味道。他偏色严重,感光度只有12。但是那种严重偏色的效果竟然对我之后的创作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这种多样性(或者说是可能性)令我止不住的去探索胶片可以形成的更多可能。之后是永恒性。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对我来说,我并不喜欢使用电子设备。我认为过度频繁的使用电子设备会泯灭我的心性。如果让我进行一些创作类的工作,我会选择纸和笔,而不是电脑软件。在我的意识里我总认为电子设备是极其脆弱的。所有数字作品,也不过是一串代码。当数据损坏,便会消失。而胶片是永恒的,它将光与影完美的收集到了它的表面上,就好像光在胶片上画了一幅画。当我按下快门时,这些光与影便被永恒的定格在了那一刻。无论过多少年,只要保存得当,这些光与影便永远都会在那里。最后是我的经历。从我的年龄来讲,我并没有全程经历过从胶片转换到数码的过程,所以对我而言这其中并没有情怀二字。但是当我第一次想要通过影像去进行创作的时候,我脑中浮现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用胶片去创作。可能与我的潜意识里的记忆有关。在我三四岁时经常在老家翻箱倒柜,经常找到那些135画幅的老底片,幼时的我便把这些胶片当作我的玩具去玩耍,于是胶片这个捕捉光与影的工具便在我的心中下了很深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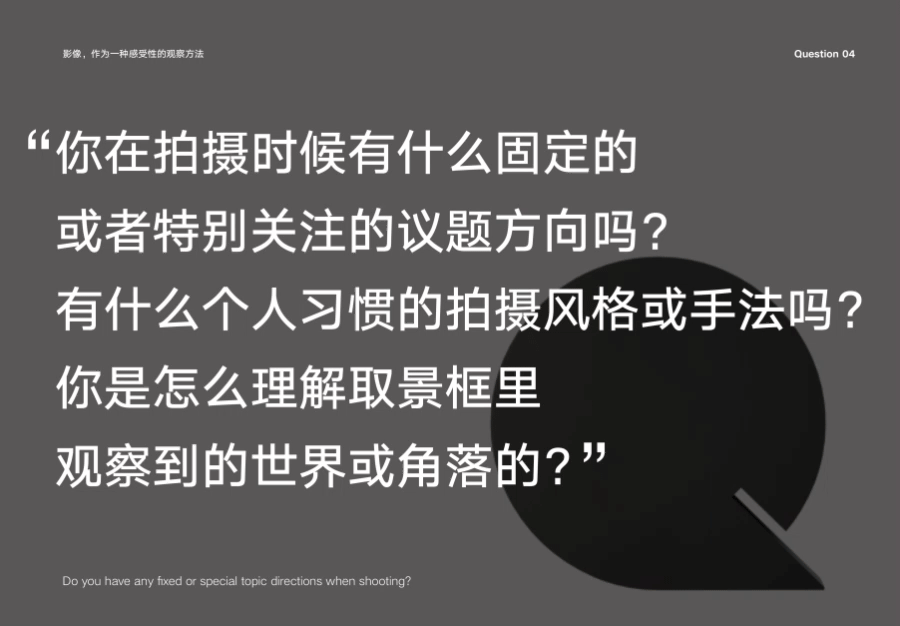
我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极端的人,极度的理性与极度的混乱占据了我的性格。这两者从来没有达到过平衡,总是一方压倒另一方或者是两者你争我抢交织错落。所以我拍摄时较为关注的点或者是想表达的方向一般都会与我的极端的性格有关。我惯于去记录这个社会中最真实的,最荒诞的,最美丽的街景与自然,有时二者相互独立,或者是二者结合。他们一般都会充斥的戏谑荒诞与平静美好的情绪。在拍摄时大部分时间我会抛弃我极度理性的那一面,不去考虑过多的影响因素,对于我来说,过多的考虑不利于我的创作。我喜欢去拍摄对比,可以是突出的光影,色彩对比,也可以是向外面的世界窥视。比如用一张照片里两个世界的方式去表达,像是打破一面牢固墙,开了一闪特殊的窗。我也喜欢用留白,或者说是暴力突出主体。戏剧化的是,我在拍摄完这类照片后的下一张往往会是一张没有主体,工整或是杂乱的物体占满整个画面的影像。对我而言,取景框里的世界是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当我的眼睛透过取景框去观看这个世界时,首先看到的是我的内心各种的情感与想法。然后我再去按下快门将我内心世界的画面记录在相机里的胶片上。每当我们用肉眼观察到了一些事物,这些事物与我们的心产生了共情,这个共情产生时,我们才会举起相机用取景框去观察这个世界。所以这时取景框里的,即使是最微小的角落也是内心在现实世界中最真实的表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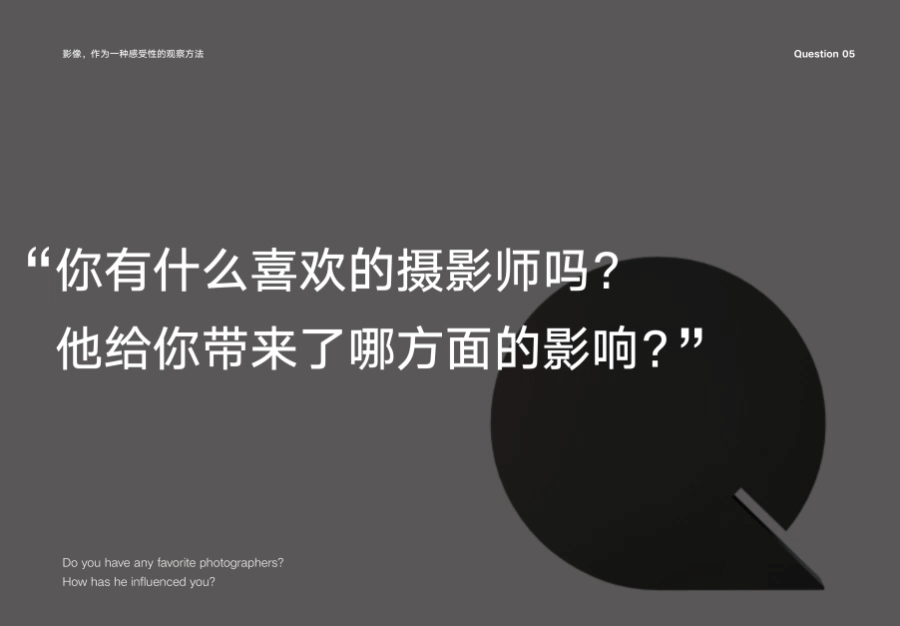
喜欢的摄影师很多,每个影像创作者都可以是我的老师。这里我列举三个对我的影像表达影响较大摄影师:森山大道,深濑昌久,乔尔·梅耶罗维茨。森山大道与深濑昌久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情绪表达,他们的作品富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每一张都包含着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作品总会使我对我个人的内心表达产生新的灵感与想法,使我的创作风格更加强烈。森山大道的理念也让我像他口中的那一条城市当中的野狗一样,毫无目的的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去寻找,去发现我最想表达的情感与事物。深濑昌久的《鸦》让我感受到的极强的艺术性与个人主观性。少了森山大道的随机性与视觉冲击感,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心灵冲击。让我发现了更多的可能的艺术性的影像表达方式。使我尝试的方法更加大胆,更加主观。乔尔·梅耶罗维茨的构图与宁静贴合了我心中极度理性的一面。。他的作品看似没有主体,但好像处处都可以是主体,他的构图美学与沉思和宁静的画面,使我在强烈的主观感情创作之余可以平静下来去深入思考我想表达的内涵所在。让我可以去创作更多的可以更深入去挖掘,去品味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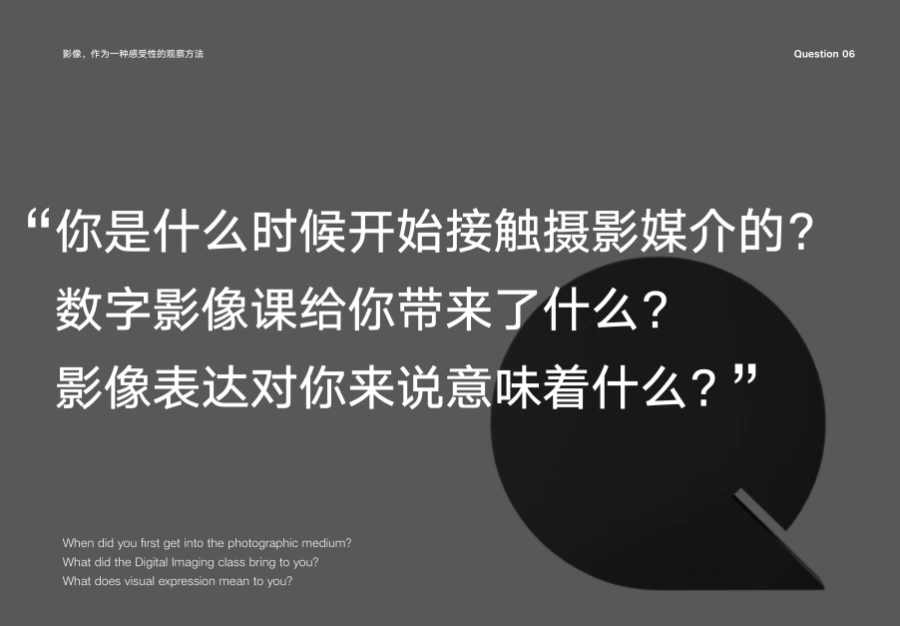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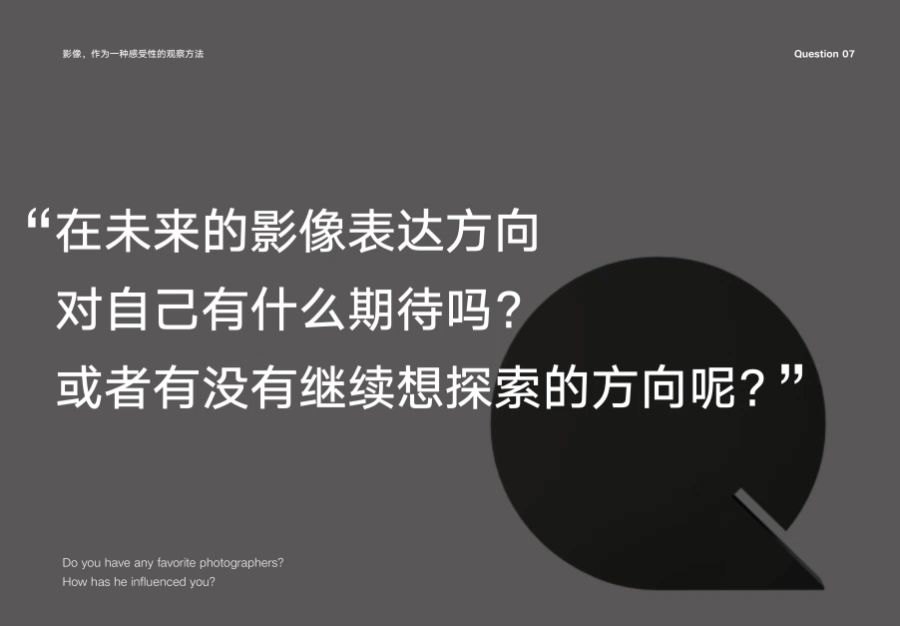
在影像表达方向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刚起步的学生,可以去表达的,可以呈现的,还有太多太多。现在碍于一些硬件设备原因,还是有很多方向没有去尝试。每当回过头看之前的作品,都会产生很多的不满意与很多的新想法。在未来我想深入一步去探索特殊拍摄方式可以带来的艺术表达的可能性。如多重曝光,长曝光等等形式将影像呈现到胶片上面。在之前的作品中,“人”的元素几乎是没有的。在接下来的作品中,我会去深入探索以的人体加以场景的形式去表达,以一种更加实验性的画面去表达,去探索人的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所产生的矛盾与一致。